 深圳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怕摇晃
深圳你大胆地往前走呀,莫怕摇晃
来源 | 摘编自《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蓝狮子出品,2021年6月出版文 | 余骏扬编辑 | 米粟
202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相比表彰与赞誉,中央送出的其实是一张新的任务单:试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无论是40年前还是40年后,人们都会问,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未停下进化步伐
1978年6月,时任交通部党组委派外事局负责人袁庚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1979年1月31日,袁庚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他对工业开发区的设想。袁庚希望,申请一片不大的土地,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只,把废旧金属卖给香港的建筑商。
袁庚提出的设想是一个药方。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经济格局中,重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为了发展资金需求量庞大的重化工业,国家不得不改变劳动力要素价值,用行政指令替代客观经济规律。加上10年动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多重问题凸显。
要建设更为健康的工业体系,也不是没有办法,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一要外汇,二有风险。袁庚主导的蛇口工业区很快变成一个试验场。蛇口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这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内地成立公司成为可能。蛇口打开的外汇渠道以港资为主,不仅相对安全,也足以让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取得关键性的突破。
▲1981年,正在兴建中的广东深圳蛇口工业区。图/新华社发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通过在一小块划定的区域内,试验新经济形式与这片土地的适配性,深圳特区诞生了。这是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也是一座面向世界的城市。
我们从工业史的视角审视会发现,深圳还是一座依靠工业而崛起的城市。从蛇口工业区开始,工业就成了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命脉。它从代工和“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响应国家宏观政策,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
富士康等代工巨头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深圳的。它们和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都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崛起,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崭露头角。
如果将视线拉远,则能看到一幅更为宏观的全球生产力迁徙图景。20世纪80年代,美国-东亚-“亚洲四小龙”的雁阵发展模型阵列,多了一个新的成员,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处在这个雁阵的尾部,蛇口工业区开启了世界资本、技术和生产能力向中国迁徙的历史进程。富士康正是对这一模式的彻底贯彻,它追逐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台湾迁徙到了深圳。
但深圳未停下进化的步伐。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的制造业已不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深圳所代表的中国“智”造不仅深入嵌套全球分工,承载了众多中低端产业链,而且在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上也逐渐强势,在一些领域能冲击世界一流水平。
雁阵现象在东亚演进
“雁阵模型”的概念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一模型对东亚的工业化历程颇具解释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它被反复提起。
简单来说,雁阵模型可被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后发经济体设法进口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提升自身的工业生产水平,此时后发经济体会大力发展代工行业,以代工品贸易发展本土市场网络。
第二阶段,随着生产技术变革,后发经济体的市场供给得到有效改善,大幅提振了人们投资发展的信心,工商业因此蓬勃发展,能够生产进口替代商品的本土工业逐渐产生。
第三阶段,随着工商业的成熟,后发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还多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因此可以大力发展进口替代的制造业,并通过出口战略赢得海外市场,实现经济的腾飞。
总体而言,雁阵模型刻画的是一种后发经济体的发展策略——通过“代工-培养产业和市场-出口”的路径实现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之后,中低产业链就会转移到更落后的经济体,让它重演上述的发展步骤。区域内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因为这种产业转移现象,形成了头雁引导后雁那样的梯级分工格局,这就是雁阵模型的大致构想。
雁阵模型发展策略曾被日本及“亚洲四小龙”采用,并取得显著的成功。20世纪50年代,日本利用产业政策形成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经济起飞。到了70年代末,日本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二战后的贫弱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经济明星。
在日本成为当时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之后,它就像雁阵里的头雁,把落后产业链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较落后的其他东亚经济体中。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日本以“经济援助”代替战争赔偿,在东亚大举开拓市场。比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韩国,也都与日本签订了赔偿支付、经济开发的协议。通过承接产业链,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水平快速提高。
▲深圳龙岗区一家工业园区的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工作。图/新华社发
雁阵模型的成功,不仅需要经济体层面的政策助推,更需要企业层面的布局和转移。政策塑造了大环境,却不是真正的经济引擎。真正让“雁群”飞起来的,是无数企业追求自我创新、避免淘汰的商业动力。
这种动力,首先来自雁阵模型内部的创新压力。
一个后发经济体要成为一只成功的“大雁”,初期势必要发展大量的代工型产业。然而代工业的门槛相对较低,代工企业的发展上限是比较低的。如果长期停留在代工层面,没有独特的制造优势,这类工厂的产业竞争力只会不增反降,容易被大风大浪击败。
所以最具备竞争意识的代工厂,一定会设法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以避免被淘汰。这类企业最终会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能生产足以替代进口货的本土商品。接下来,这些升级的代工厂就会在其他落后经济体中寻找新的成本洼地,迁出本土的生产线,从而塑造出区域内不同经济体的梯级分工。企业层面的不甘沉沦,在宏观层面上最终就会变成产业转移潮。
1980年前后的中国内地,恰好承接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产业转移潮,并通过这一波机遇逐渐形成强大的内地市场。这个进程包含两个核心要素——
一是上一波雁阵效应的受益者,也就是那些成功靠代工做起规模、打算将生产线外迁的企业;二是中国内地的开放区域。这两者虽然属于层次、形式、规模完全不同的实体,但却共享同一套发展规律,也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构性问题。
甚至可以说,读懂了那些成功的代工企业,也就能读懂深圳乃至中国的发展格局。
“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
成立于1974年的富士康集团,它的发展壮大和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着深切的联系。富士康的发展经历了台湾-深圳-大陆腹地几个阶段,这种迁徙过程是经济学里雁阵模型的极佳模板,它深刻体现了一家企业为了获得最经济的生产资料而与资本、技术一同在地理空间上迁徙的过程。
为了追逐新的成本洼地,迁出本土的生产线又塑造出了新的梯级分工;正是企业和企业家层面的不甘沉沦之心,产业转移浪潮出现,新的城市随之诞生。
正因为富士康的极致成本管控,它崛起并成为“代工之王”;它的辐射范围扩大,也见证了东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中国大陆地方政府的工业发展及土地开发冲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台湾的经济由于参与世界分工而迅速发展,但这也必然带来人力成本的飞涨。比如到了80年代末,当地基本工资已经超过2500元人民币,但当时中国大陆的工人月薪只有500元左右。巨大的成本差距,自然会让台商迅速注意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土地广袤,而且缺乏开发。相比之下,台湾的土地价格节节上涨,对于需要扩建厂房、增置设备的企业而言,土地成本实质上压抑了他们继续投资昂贵进口设备的需求。
许多台商希望找到新的成本洼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是潜在的可能选项。
不过在80年代,台商对改革开放仍然持相对观望的态度,只有不多的台商前来探路。郭台铭最初在深圳的投资比较保守,多少反映了当时资方的心态。但在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信心迅速高涨起来,纷纷增加了在大陆的投资。
▲工人在富士康工厂车间。图/新华社发
1993年,郭台铭看上了邻近深圳市区的龙华镇。有关这位商人的传记里曾描写过戏剧性的一幕——郭台铭振臂一挥,说:“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此后,富士康启用龙华科技园,在这里逐渐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综合生产基地,支持包括计算机、游戏机、服务器、主机板、网络配件、光通信组件、液晶显示器、精密模具等工业品的生产。本地研发、生产线外迁的模式,显然为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长。
而对深圳来说,富士康的入驻相当于为这片土地激发了雁阵模型的内生动力。
雁阵模型之所以是一种有效的发展策略,固然是因为有“头雁”转移产业的驱动力。但如果没有无数不甘于乖乖做代工的“后雁”,“雁阵”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在深圳大力发展代工产业的浪潮之中,应该有着无数类似青年郭台铭那样充满渴望的眼睛,观察着如何才能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最终打响自己的品牌。这些不甘沉沦的心灵,最终逐渐形成了深圳本土企业创新的种子。
随着富士康在大陆的扩张,由于它对价值洼地的强调和对成本的极端管控,这家公司又遭遇了新一重的困境。
同样的情况在深圳也会出现。在发展水平逐渐提升后,以“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代工产业的未来也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问题。
代工拷问与深圳创新力
也许会有人想起,在iPhone刚刚面世的阶段,富士康和深圳曾经以一种让人担忧的面目共同出现。
2006年6月,英国《星期日邮报》推出一篇影响甚大的报道——《iPhone之城》。这篇报道指出,深圳的富士康龙华工厂拥有20万名员工,人口比英国港口城市纽卡斯尔还多。但这座巨型工厂的员工的生活状况却让人担忧——他们住在被严格管理的宿舍里,而且每天工作15个小时。这些工人以女工为主,月收入不足400元人民币。
这篇报道引起了国内媒体的追踪报道,被视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向其中一家媒体发起了一场索赔额高达3000万元的诉讼官司。这场官司更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强烈愤怒,在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之后,富士康和它起诉的媒体达成了和解。
某种程度上,这场风波隐喻代工经济的风险。媒体对女工产生的同情与愤怒,反映着社会平等意识逐渐加强。这正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代工经济优势减退的社会背景,是富士康成长之路上必然遭遇的困境。尤其是对深圳这座在经济上越来越成功、积累起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城市来说,以代工产业为主的“血汗工厂”,还应不应该是这座城市的重要经济引擎?
通过廉价劳动力赢得比较优势的后发经济体,最终必须选择自己的出路——是继续以出口为命脉,成为“外贸之城”,还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成为“创新之城”?
“雁阵”的同构性总会制造出有趣的巧合。正如郭台铭在创业初期不甘心做普通的代工厂,在提升创新能力上下足了苦功,深圳在发展战略上,也从承载国际产业转移转向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路线。
实际上,正是在《iPhone之城》刊出的2006年,深圳本土的民企已经逐步崛起。在2005年,深圳的GDP已经突破4000亿元,超出“十五”计划目标3000亿元33%。在这一年,深圳的进料加工贸易增长开始回落,侧面反映了深圳工业的转型升级,也说明了深圳增长数据的背后,本土民营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日益强大。
深圳民企的发展,和先前代工经济为主的阶段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代工产业的经验积累,使得深圳的模具、配件、元器件供给非常丰富,涵盖制造链条的上下游。这样一来,科研成果的产品化和商品化在深圳就会变得相当便捷,创新型的企业也就更容易在深圳成长起来。
目前,通信产业、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医药产业的产业链和配套已经在深圳成熟起来。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不仅包括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等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大企业,也有许多具备成长性的中小企业。2014年,福布斯对中国内地城市进行创新能力排行,深圳高居榜首。2016年,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超过1.8万件,连续13年位居中国内地各大中城市之首。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数据,是深圳在科研投入方面的魄力。
深圳在研发上存在一个先天劣势,就是缺乏优质的大学群。所以如果考察深圳的研发经费与GDP的关系,会发现深圳的研发经费强度显著低于高校林立的北京。但深圳的创新能力仍然非常强大,因为它的工业企业研发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比如,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800亿元,占GDP的4.1%,足足比国内平均水平高1倍。
回顾深圳和富士康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层面、不同体量、不同形式的存在,它们都遵循着相似的发展规律——把自身作为创新主体,形成比较优势后逐步杀入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最终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在迈向创新型经济的路上,它们曾经赖以成功的代工能力将逐步被剥离,转移到其他渴望繁荣的后发经济实体。
▲图/视觉中国
“特区不特”启示录
深圳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就遭遇过众多质疑、唱衰与反对,这些阻力实打实地挡在深圳的前头,是一道道必须迈过去的坎。
20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创立之初,围绕经济特区的争论焦点,在于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坚定了特区的发展方向。经过后来20多年埋头苦干的实践,特区逐渐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让中国在开放的过程中调节自身原有的管理能力和体制,是有效的改革设计而非结构性的错误。迈入21世纪之后,质疑特区“姓什么”的声音基本不存在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候,特区经验复制到全国,特区的功能是否应该保留,就成为新的争议。
当时,国内出现了特区还要不要“特”的争论,且一度甚嚣尘上。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甚至就冲在这场争论的最前线。
后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申:“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定调“毫无疑义特区还要‘特’”,但与此同时“原来主要靠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而形成的特区的一些特色,自然要有所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结束了“特不特”的争论,把率先进行制度创新视为新的竞争优势。这也是后来深圳大力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人才政策的原因。
进入21世纪,随着长三角经济带的崛起,深圳有过一波企业总部迁沪的浪潮。热爱深圳的新深圳人们不甘沉沦,民间陆续抛出“深圳,你被谁抛弃”“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等争鸣篇章,指出深圳的成功之道,大力呼吁深圳人抖擞信心,找到深圳乃至珠三角新的经济突破口。在这些文章所擘画的愿景中,已经隐约有了今日“大湾区”的格局。
回顾深圳与各种“唱衰”潮流对抗的过程,似乎能梳理出一条精神秩序上的脉络——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官员,再到民间,所有人的心都凝聚在向前发展的意志上。国家自上而下的、对深圳特区之“特”的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根本方向性意义的价值承诺——向前看、大胆闯。
这种上下相向而行的发展共识,正是深圳一次次战胜“唱衰”的精神力量,也酝酿了深圳孵化出众多优秀本土企业的社会氛围。发展共识和对进步的渴望,驱动中国崛起的深圳的这种发展价值观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共识的一个缩影。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能理解为什么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给深圳的不是庞大的投资项目,而是一份期望深圳在诸多方面探索经验的任务表。因为深圳的使命,从一开始就是以一座城市的身份,扮演中国这个格局中独一无二的“创业者”角色。
学习深圳早期的进口替代战略来快速发展区域经济,是相对简单的;但如何适应当下全球竞争,为中国后发城市提供新的思路与突破口,完成深化改革的宏伟目标,这个问题,正有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为全国交出新的答案。
《中国基本盘》,何丹、徐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蓝狮子出品,2021年6月出版
本文摘编自《中国基本盘》,本书通过分析区域发展的经典模式,探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如何推动大国复兴,在新发展格局下从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到世界制造强国之路如何演进等命题,包括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崛起与反思,中国制造升级之路,产城竞合模式的变革,等等。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书中内容,请在评论区留言,财叔准备了三本《中国基本盘》,分别赠予评论区点赞量最多的前三名读者(点赞数统计截至下周六22点,为让更多人享受财叔的福利,每人三周内只能获赠一次)。
感谢各位的关注,财叔会为大家推荐优质好书,或许下次中奖的就是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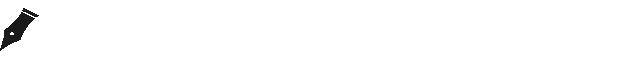
觉得内容不错
来个“一键三连”——分享、点赞、在看
看完不吐不快,就给我们留言吧
留言点赞多有惊喜